|
理财通 http://njqzwd.com
离开园子渐久, 思念也慢慢开始变成一种痛, 像游子突然听到天际间苍凉的鸽哨声…… ——题记 清华园的美,很大一部分归因于其建筑。 清华园的早期建筑很安详,建构了一个独特的世界。一是西式建筑,二是古典园林。它们相安相生在一个园子里。这个园子如同一个婴儿,它是要长大的。 今日的清华园已经有106岁了。 园子是有生命的,它如同一个人,有自己独异的气质。 清华园的气质是什么呢?它的建筑无声地言明了。它的底蕴是中国古典的,有皇家的气息,同时又进驻了西方的文明。整个中国恐怕找不出第二家了。
清华园诞生在1911年。到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,它已如一个活泼有生气的少年。翻看一下那时的清华园老照片,那时园子里走动的人们。虽然是一个飘摇战乱的年代,但是园子里处处透着安详。 园子里孕育着希望和生气。 清华国学院的灿烂不是偶然。清华园滋生、润长了那么多青年才俊,也不是偶然。 关肇邺先生说:“建筑可以潜移默化影响一个人,乃至塑造一个人。”在这样的园子里,里面的人有谁不受它的滋润? 在古中国,建筑总与堪舆联系在一起不是没有缘故的。建筑的式样,布局建构了一种环境,这样的环境无形中形成一种气场,这种气场无形中影响着生活其内的人们。这种气场或许就是古时所称的风水。 清华园的气场是在变的。随着时间变,随着时代变。它的变又体现在建筑的变。拆掉一些旧的建筑,建起一些新的建筑。 清华园至今让人愉悦、赞美,在于一些百年前的老建筑没有被拆掉,保持了原样。比如老图书馆,清华学堂,体育馆,科学馆,大礼堂。也就是说,由建筑构成的百年前的清华园的气场还在。
清华园是一个生命,它是要延续的。 1914年,清华园的总体设计交给了一个叫亨利墨菲(HenryKillamMurphy)的美国人。这一年他刚到中国。他是耶鲁大学建筑系的学生。那时的清华园还是一个废弃的荒园。废弃的河道、池塘,长满野草。精美的石桥、游廊、庭院无声地诉说着往昔的皇家胜景。 清华园当时是一所留美预备学校。墨菲就在这个荒败的园子上建起了一座美国学校。西式建筑在中国古典园林里似乎并没有水土不服,而是相得益彰,它们相互映衬出彼此的好来。 墨菲设计的西式建筑多采用古典手法。比如大礼堂采用古罗马、希腊的建筑式样,运用立柱,拱券,穹顶为设计要素;体育馆、科学馆、图书馆采取了文艺复兴时期古典建筑的手法。西方古典建筑给人宁静之感,它与中国园林在精神上是相契合的。同时它又给人肃穆、庄严之感,仿佛是沟通人与天的中介。园林曲径通幽,效法自然,也是企图达到天人合一。
两种建筑代表了两种思维方式,但它们间又是相通的。正如吴冠中先生所说:“中西方的优秀艺术是哑巴夫妻,虽语言不通,但爱情是甜蜜的。”清华园的美或许就是这种爱情的见证。 看一下早期清华园的图片或建筑手绘,很容易为那种静谧感染,但分明又感受到它如少年般蓬勃的朝气,潜伏和孕育着希望。中国园林与西式建筑共同营造了这样的氛围,它宛若一首清新动人的小诗。 到了三十年代,墨菲设计的图书馆已经不能满足师生的使用,需要扩建。从美国留学归来的清华学生杨廷宝主持设计,那年他30岁。 杨廷宝沿用了墨菲的设计式样,新楼与旧楼呈垂直分布。他巧妙地用一个45度方向的4层高的中楼将两者无缝衔接,新楼与旧楼便浑然一体。如果不了解这段建筑史,人们立足于前,很容易将它们看为同期建筑。 杨廷宝为清华园新添了一座建筑,但它悄无声息地隐没在旧建筑里。它是原有清华气场的延续,但又添了新的生机。
杨廷宝喜欢安静与古典 图书馆的扩建只是杨廷宝受命做清华园二期总体规划的一小笔,但它投射出杨廷宝的设计思路,那就是延续墨菲的设计,将清华园的这首诗写下去。他不想破坏这首诗的格调、氛围,而是要渲染、壮大,焕发出一个新生命。 受战争的影响,杨廷宝的总体规划并没有全部实现。但是,他主持设计的生物馆、气象馆、学生宿舍明斋还是建成了。这些建筑古朴、简洁,依然沿用了西方古典建筑的风格。这些新建筑与已存在的旧建筑一脉相承。 遗憾的是另一些建筑没有按规划落成,比如在荒岛中央筹建博物馆,环湖辐射状布置五栋特种学术建筑(生物馆只是其一),北部小河北岸另布置三栋特种学术建筑(化学馆只是其一)。除荒岛南端,校门入口处保留部分自然地形、山水花木之外,荒岛四周采用规则半圆环状水渠与整齐对称的道路系统。这一荒,就再也没动过。 杨廷宝性喜静,他对古典艺术手法有自己独到的领悟和妙用。除了个人禀赋外,还要归功于他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所受的建筑学教育。当时,宾大聘请了大量的巴黎艺术学院培养的建筑师,他们很看重设计的艺术性,它成了衡量学生是否足够优秀的一个很重要的砝码。 杨廷宝极高的艺术才能很快让他脱颖而出。这或许和他自幼的家庭教育和先天禀赋有关。他的妈妈能书善画,是米芾的后代。他很小的时候就表现出卓越的绘画才能。在清华园读书时,老师希望他到美术学院留学,可是他选择了建筑。 在宾大,杨廷宝用两年半修完了四年的学分。他的设计获得两次金牌,多枚铜牌。在1924年,他的设计又获得爱默生一等竞赛奖。毕业后,他自费到欧洲旅行半年,专门考察西方建筑。 杨廷宝的个人气质和修养无疑是和清华园相契合的,清华园的二期总体规划设计交给他是再合适不过了。从他未完成的二期设计来看,他的新作品不仅巧妙地与原建筑融为一体,而且更为清华园平添了几分静穆之美。 他可以称得上是一位建筑诗人。 到了八十年代,清华园图书馆又面临容量扩增的问题。关肇邺先生1983年得到委托设计的受命,1991年新图书馆落成。关于新馆的设计,他很想询问一下杨廷宝老先生的意见,可是就在他得到受命前不久,杨老先生故去了。 我想关肇邺先生是熟知杨廷宝先生的设计的。即使他没有听到杨廷宝老先生的意见,但从现有建筑设计来看,他是秉承了杨老先生的设计思路的。那就是新建筑不是标新立异,而是原有建筑群生命的延续。这一点杨廷宝先生做到了,关肇邺先生也做到了。
建筑诗人关肇邺先生 关肇邺先生阐述设计思想,在他看来,很重要的一点是“和谐”。“和谐”着眼点显然不是单体的建筑,而是建筑与建筑间的关系。他从建筑群之间的关系来设计单体建筑的式样及其布局。这一点无疑是很高妙的。 关肇邺先生的设计讲究建筑的环境及其营造的氛围。他关注单体的建筑存活在怎样的环境里,思考它怎样与周围环境谐和匹配,同时它自身又如何散发独异的气质,影响周围的环境,使环境或氛围更趋于一种美的境地。 其实,这样的建筑思想其实是想用建筑作为句子,写下一首诗。诗是讲求美和境界的。这样的建筑思想也应和了中国传统中的“和而不同”。“和而不同”才是君子,如兰,如莲,如梅,如竹。 中国传统建筑的营建很讲究氛围,格调。这是一种建筑的传统。建筑从来不仅仅为满足实用居住功能的房子。 去年夏我偶然到访了楠溪江,意外发现了古村落。这些古村落据说从宋就有了。这激起了我极大的好奇。走进这些古村落,我宛如走进一首诗里。虽然它凋败,它破落,但依然可见往昔的格局,它意图营造的氛围。在这样的环境里,人心很容易静下来,向善,谦和,感恩。
楠溪江古村落长廊 一个深山里的小村落的布局和设计都如此讲究。河道、水榭、游廊、庭院、戏台、私塾、古木,它们恰到好处各就其位,走在其内,宛若画中游。这里的长寿老人很多。谁说它不是一个桃花源? 清华园,它是旧时皇家园林。当然它远非一个小村落比得。墨菲对清华园的规划,并没有破坏原有残剩的园林。一个西方人懂得对东方文化的尊重。清华园的美很大一部分得益于此。中国的建筑营造向来脱离不了文学的诗性。诗性的背后又是强大哲学的支撑,那便是天人合一。 关肇邺先生最难能可贵的是对传统的承续。现在的建筑学与文学渐离渐远,有文学修养的建筑师不多见了。关肇邺先生可能是最后一批受传统文化浸染且懂其髓的建筑人。此后,这样的人恐怕再也见不到了。在我心目中,他比大熊猫珍贵百倍。他这样气质和谈吐的人恐怕会成为历史。 关肇邺先生是1929年生人。他有幸见到林徽因、梁思成先生,成为他们的助手,而且有一段时间就在梁、林两位先生家里工作。他也有幸见到且耳闻梁、林客厅里大学者们的高谈。这些对今天的我们都是奢侈,那是一个群星毕现的时代。
梁思成1928年法国 关肇邺的父亲关赓麟是清末的一位进士,后来官居要职。他曾随政府要员到欧美九国考察宪政。考察团后来给清廷的报告中有这样一句话:“宪政有利于国,有利于民,而最不利于官”。他将自己大半生给了中国的铁道和教育事业。
关赓麟 晚年,关赓麟回归文学,创建“稊园诗社”。稊园诗社不乏文化巨擘、国学大家。从成立到消亡,聚集了当时南、北百多位中国顶尖文化名流。稊园诗社可以认为是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规模最大、参与的重要文化人物最多、各不同学术流派交流、合作最为和谐、存续时间最长的文学社团。
稊园诗集 关肇邺先生很少提及他的父亲,只说他是一位旧文人。这是关先生为人的谦和。他书房的墙上挂着父亲的书法作品。当然,他还是一位重要的诗人。
关赓麟先生的书法 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长大,又亲临梁、林两位先生,加之个人独异的禀赋,共同成就了关肇邺先生。他有一种独特的魅力。在他身上,我依稀看到了梁、林两位先生。他们的气质和谈吐一部分存活在关先生身上。这样的品质在当今很稀缺了。 清华百年校庆后,新建了很多建筑。引入国际建筑大师的设计。当然每件作品都美轮美奂。但是,它们合在一起的时候,我总觉得少了些什么。对,那就是建筑早已失去的诗意。 2017年夏末DAN-EU 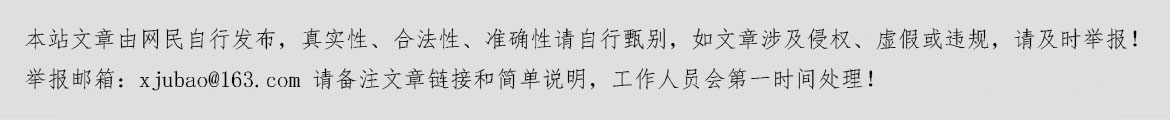
|
|
1
 鲜花 |
1
 握手 |
 雷人 |
 路过 |
 鸡蛋 |

业界动态|久易新闻网

2025-11-04

2025-11-04

2025-11-04

2025-11-04

2025-11-04

请发表评论